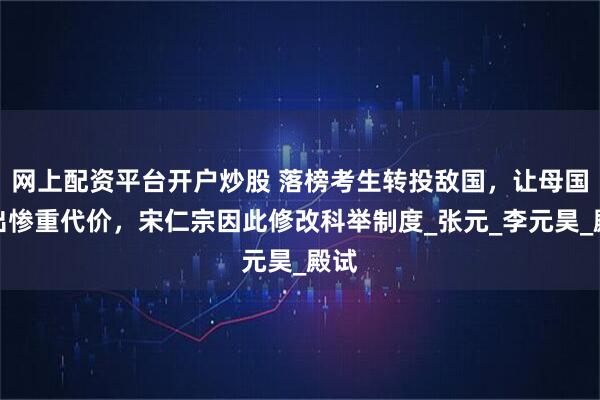
北宋仁宗年间,有一位落榜的士子,因屡试不第,心灰意冷,竟然踏上了一条背离故国的道路。他的名字网上配资平台开户炒股,在大多数史书中被刻意隐去,人们只知其号“张元”。那么,一个落第考生,如何变成了大宋的心腹大患?
张元,本名不详,陕西华阴人,自幼聪慧好学,尤擅辞章。他自称“负气倜傥,有纵横才略”,在当地小有名气。可惜,才名虽响,却始终未能入仕。他屡次参加科举考试,虽曾通过“省试”(相当于会试),却在最后的“殿试”中名落孙山。
这在当时的北宋前期,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不同于后来的明清时期进士“只分高低、不分生死”的录取方式,宋代殿试实行末位淘汰制。省试过关,并不等于金榜题名。若殿试失败,一切从零开始。
张元的命运,便在此转折。一个心高气傲、屡败屡战终无所成的文士,终于心生怨愤,决定以另一种方式“成名”。
展开剩余80%张元并非孤身一人。他有一位同道好友,名叫胡某,两人合谋,开始策划一场“行为艺术”。他们刻意制造轰动效果——在石板上刻诗,大肆宣扬怀才不遇之愤,在街市之中痛哭流涕、捶胸顿足,引得众人侧目。
这类举动,在当时并不稀奇。古人重视名节,读书人若不得志,往往采取极端方式博取上官青睐。张元和胡某这番“表演”,果然吸引了当时一位边地大吏的注意(后人多认为是韩琦)。
然而,二人最终未能如愿以偿。那位官员接见他们后,并未看到“非常之才”,仅将他们礼送出境。
失望之余,二人决定“转战他国”。他们选择的目的地,正是当时的强敌——西夏。
西夏建国在即,正值李元昊扩张国势、招贤纳士之时。二人化名张元与吴昊,径直进入西夏都城兴庆府,再次上演“故技”。
不同的是,这一次他们犯下了一个极为“大胆”的错误:在酒楼墙上题诗留名,“张元、吴昊来饮此楼”。此举触犯了西夏国主李元昊的名讳——“元昊”二字被视为大忌。
两人随即被西夏军士逮捕,作为“疑似间谍”带到李元昊面前质问。
张元并未慌乱,反而妙语反击:“姓尚未理会,乃理会名耶?”一句话暗讽李元昊“姓赵还是姓李”都未曾搞清,还计较百姓名字,可谓一语双关。
李元昊非凡之主,听罢反觉有趣。他得知二人是自宋来士子,更生起“用敌之才”的念头,于是破例启用二人。
自此,张元开始飞黄腾达。他很快被提拔为太师、尚书令、中书令三职兼任,地位仅次于李元昊本人。公元1038年,李元昊正式称帝,张元遂被封为西夏国相,统筹国政、筹划军略,成为西夏政坛核心人物。
为了争取西夏朝中保守派信任,张元积极为李元昊出谋划策,尤其在军事与外交上力图对抗宋廷。他深知大宋军政体系之弱点,对故国展开了一连串精密打击。
在张元主导下,西夏自1040年起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对宋战争:
三川口之战(1040年):李元昊率军突袭大宋边境,宋军全军覆没,伤亡惨重。 好水川之战(1041年):这是张元一手策划的经典伏击战。他诱导宋军统帅任福轻敌深入,结果宋军前后夹击,全线溃败,任福战死。 定川寨之战(1042年):再次以伏击战术击败宋军,造成万余人阵亡。其中,好水川之战尤为著名。张元设计佯攻怀远,吸引宋军主力追击,再于好水川伏兵突袭,一举击溃宋军。战后,张元题诗一首,讽刺韩琦、夏竦等宋将:
“夏竦何曾耸,韩琦未足奇; 满川龙虎辇,犹自说兵机。”署名赫然写着:“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题”。这一行为,被宋人视为赤裸挑衅。
这场战争中,还有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汉人军官——韩福。他原名韩怀亮,出生于西夏境内的汉族家庭,因不愿臣服李元昊,毅然投奔大宋,改名韩福。
他在好水川之战中随任福一同阵亡,被后世赞为“慕义洁身”。与张元等人形成鲜明对比。
《春秋》大义“去夏就夷”为不忠不义,后人曾这样评论张元:“张、吴以中国士人甘投夏国,律以《春秋》去夏就夷之义,罪岂能辞?”而韩福之节,反显其可贵。
张元晚年忧思成疾。在李元昊称帝后,他屡次劝其改“劫掠为占领”,主张绕过西北防线,从西线深入关中,一举夺取长安,以图国力根本之变。
然而李元昊更倾向“掠夺式战争”,既省事又见效快。加之西夏经济困窘、军力紧张,无法支撑大规模长期战役,张元的战略终未被采纳。
1044年,宋夏“庆历和议”达成,边境战火暂息。同年,辽国大举入侵西夏,破坏了辽夏盟约。内外交困之际,张元郁郁而终。其同伴吴昊,最终下落不明。
张元虽通文艺,但因其叛国行为,其诗作在宋以后历代文集中均遭屏蔽。现仅存数首,其中最著名的《咏雪》:
“五丁仗剑决云霓,直上天河下帝畿; 战罢玉龙三百万,败鳞残甲满天飞。”诗中气势恢宏,却难掩其身份之尴尬。
这场因一位落榜士子引发的战争,让宋廷深感教训。仁宗最终决定改革科举制度:取消殿试末位淘汰制,将未被正式录取者列为“同进士出身”,以防人才流失,酿成更大祸患。
发布于:广东省锦鲤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